【專題】巡禮馬銜山玉文化與文學(xué)融合發(fā)展考察活動(dòng)
《禹王書》:原始?xì)庀ⅰF(xiàn)代情調(diào)與荒誕主義的巧妙融匯
鄭瑩
馮玉雷的重述神話創(chuàng)作展現(xiàn)了一種先鋒實(shí)驗(yàn)精神,主要表現(xiàn)為在與傳統(tǒng)渾融共生的基礎(chǔ)上,嘗試突破不同文體和不同文化形式之間的壁壘,在“原始?xì)庀?rdquo;“現(xiàn)代情調(diào)”和“荒誕主義”的藝術(shù)張力中,探尋表現(xiàn)技藝、美學(xué)風(fēng)格與價(jià)值觀念的創(chuàng)新。這也彰顯了當(dāng)代作家試圖通過精湛的文藝作品,推動(dòng)中華優(yōu)秀文化資源創(chuàng)新性發(fā)展和創(chuàng)造性轉(zhuǎn)化的社會(huì)擔(dān)當(dāng)和文化自覺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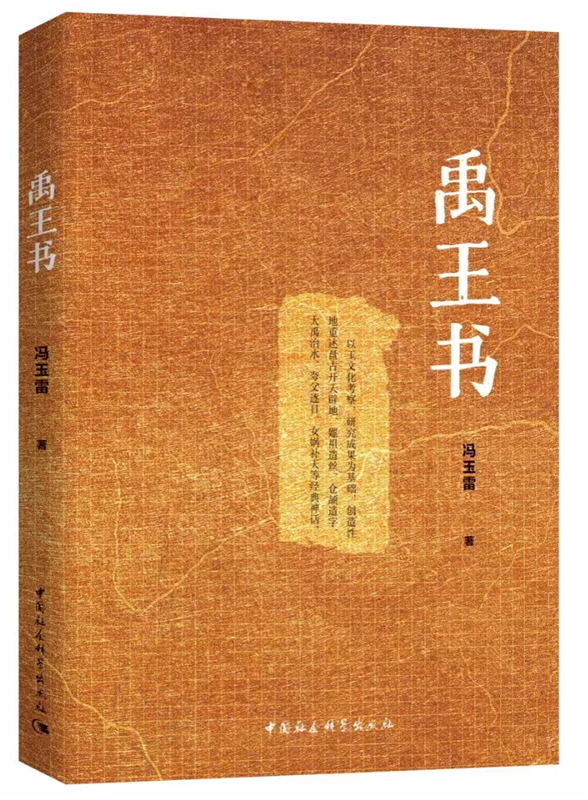
首先,直觀體現(xiàn)為以神話介入現(xiàn)實(shí)。魯迅在《中國(guó)小說史略》中稱,神話是原始初民對(duì)自身無法掌握現(xiàn)象的解釋。由此可見,除了虛構(gòu)性這一基本特性外,現(xiàn)實(shí)性也是神話誕生的根基之一。在《禹王書》中,神話原型不僅成為連接眾多文化要素的橋梁,更成為作者介入現(xiàn)實(shí)、觀照人性的重要載體。
如作者借用了黃帝始祖神話母題,賦予“銅”這一意象深刻的文化內(nèi)涵與反諷意味。在小說中,銅不僅代表著物質(zhì)實(shí)體,更成為欲望和外來文化的象征。部分部落首領(lǐng)對(duì)銅持負(fù)面看法,認(rèn)為它是導(dǎo)致物欲橫流、民風(fēng)敗壞的元兇之一,并且作為外來物的紅銅對(duì)本土其他文化形態(tài)構(gòu)成了威脅。四岳曾向鯀發(fā)出警告,強(qiáng)調(diào)玉石與彩陶的相互扶持是抵制銅文化擴(kuò)張的關(guān)鍵,他堅(jiān)信本土燒制的“陶”才是中華民族永恒的根基。然而,作者借重華之口,諷刺了片面看待問題的社會(huì)現(xiàn)象。重華認(rèn)為,盲目排斥銅是一種虛偽且可恥的態(tài)度,我們應(yīng)以辯證的眼光看待物質(zhì)。他指出,物質(zhì)并不局限于財(cái)物或外來物,自然萬物如日月星辰同樣屬于物質(zhì)的范疇。人類自古以來都在追求與物質(zhì)和諧統(tǒng)一,既然銅器在實(shí)際應(yīng)用中展現(xiàn)出了比石器和陶器更強(qiáng)大的功能,我們?yōu)楹我獙⑵湟暈楹樗瞳F呢?此外,黃帝還曾用銅針治愈了毓土等人,而販銅者也是通過合法勞動(dòng)獲得財(cái)富的,他們又有何錯(cuò)?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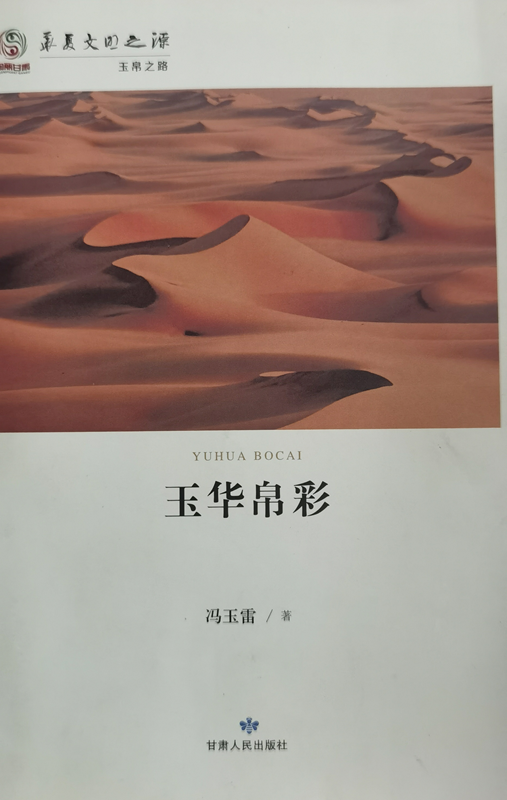
再如,馮玉雷將女媧造人神話和補(bǔ)天石神話與當(dāng)代教育現(xiàn)狀相結(jié)合。女媧將補(bǔ)天剩余的那塊石頭命名為“熊”,而“熊”又是啟的乳名。為了給孩子營(yíng)造一個(gè)良好的成長(zhǎng)環(huán)境,女媧創(chuàng)造了雞、狗等牲畜作為陪伴。在初七那天,她用泥土塑造出了自己心目中的“熊”。然而,在黃帝、桑林等人看來,這些泥人不僅需要滿足合婚生育的需求,還應(yīng)掌握各種技藝,如吹拉彈唱、耕作放牧等。但女媧認(rèn)為,她所創(chuàng)造的“熊”應(yīng)該是吃苦耐勞、儒雅有度等優(yōu)良品質(zhì)的繼承者。女媧反駁黃帝的情節(jié),實(shí)則巧妙地諷刺了社會(huì)中過分追求表面成績(jī),而忽略德育的急功近利的教育行為,警示人們應(yīng)當(dāng)注重教育的全面性和長(zhǎng)遠(yuǎn)性,避免陷入短視和片面的誤區(qū)。
其次,夢(mèng)幻世界的意識(shí)流書寫是原始經(jīng)驗(yàn)的映現(xiàn)。馮玉雷深受交感互滲神話思維的影響,他通過夢(mèng)幻原型的置換變形,打破了文本的時(shí)空界限、邏輯框架以及主客體的對(duì)立狀態(tài)。夢(mèng)者思緒更同琴聲、鼓聲等動(dòng)態(tài)聲音表象互通共感,使讀者仿佛置身于一個(gè)交感互滲的超現(xiàn)實(shí)主義境界中,沉浸于原始主義的濃郁氛圍和荒誕主義的獨(dú)特基調(diào)之中。
以“美人幻夢(mèng)”原型的置換變形為例,“所謂‘美人幻夢(mèng)’,指用幻境或夢(mèng)境表達(dá)情思與性愛主題的創(chuàng)作類型。”小說中,巨大的心理波動(dòng),如恐懼、悲傷、思念等,是夢(mèng)者踏入夢(mèng)饜或幻境的前兆。馮玉雷不僅將幻夢(mèng)者的范疇擴(kuò)大至所有角色,無論男女。還在情思與性愛主題的基礎(chǔ)上,摻雜了神話預(yù)言的成分。如大禹與女媧初見之景,實(shí)則是大禹夢(mèng)境的生動(dòng)再現(xiàn)。如憂喜交加的巨大情緒波動(dòng),使女媧常處于半夢(mèng)半醒的狀態(tài),而她所夢(mèng)之事竟都戲劇性地成了現(xiàn)實(shí)。熱戀時(shí)期,她常夢(mèng)到與大禹分離,最終,大禹也因治洪大業(yè)離她而去,被迫分離的兩人通過鰲鼓聲與夢(mèng)境傾訴思念之情。又如,睡夢(mèng)中的脩己隨著嫘祖彈奏的《云門》樂曲,深陷逐鹿之戰(zhàn)的夢(mèng)饜之中。小說中,馮玉雷巧妙地將琴音的節(jié)奏與脩己的心理情感節(jié)奏相融合。起初,沉悶回蕩的琴音為戰(zhàn)前的緊張局勢(shì)營(yíng)造出濃厚的氛圍。此刻,夢(mèng)中的脩己恍若置身迷霧之中,吶喊、武器碰撞、骨骼斷裂之聲交織在一起,連綿不絕。馮玉雷通過大量短句的集中出現(xiàn),直觀展現(xiàn)了脩己恐懼無助的心境。隨后,七弦琴在玉磬、陶玲等樂器的伴奏下悠揚(yáng)響起,琴聲渾厚靈動(dòng),凝重蒼勁,夢(mèng)中的世界也隨之變得明朗寧?kù)o。頃刻間,平緩的琴聲時(shí)而激揚(yáng),時(shí)而低沉,映襯出士兵們發(fā)現(xiàn)脩己時(shí)驚愕迷茫的復(fù)雜情緒。突然,琴聲驟變,如泣如訴,如怒如歌,淋漓盡致地表現(xiàn)了脩己在希望與掙扎中尋求出路的心路歷程。最終,這場(chǎng)殘酷的戰(zhàn)爭(zhēng)竟因脩己的突然出現(xiàn)而草率停戰(zhàn)。更為荒誕的是,休戰(zhàn)雙方立即加入幫助脩己拼接銅紋飾的行列中。

最后,表現(xiàn)為“書”體及后現(xiàn)代含混拼貼話語(yǔ)方式的使用。馮玉雷接受采訪時(shí)提及,現(xiàn)代文明的符號(hào)不斷提醒他面對(duì)現(xiàn)實(shí),然而,那些偶然映入眼簾的老城、廢棄的大油罐等景象,不經(jīng)意間又激發(fā)了他內(nèi)心深處的原始本能與情感。為此,他決意打破時(shí)空界限,如同米羅一般,徹底“打破立體主義的吉他”,將眾多原本不相融的元素巧妙地組織在同一畫面中,追求它們和諧共存的理想生態(tài)。《禹王書》中,作者特意選擇了書這一種自由度高的文體。與其他文體相比,書體在書寫對(duì)象、文體規(guī)范及情感表達(dá)等方面展現(xiàn)出了無拘無束的特性。正如劉勰在《文心雕龍·書記》中記載,“書者,舒也”,“夫書記廣大,衣被事體”。

雖然其外表帶有神話小說的色彩,但隨作者書寫對(duì)象的轉(zhuǎn)變與情感的抒發(fā),它自然而然地融入了散文、考察筆記、詩(shī)歌以及游記等文體特征。同時(shí),隨作者的發(fā)散聯(lián)想,穿插許多史料文獻(xiàn)進(jìn)行解釋性敘述。而與書體相對(duì)應(yīng)的是,小說的語(yǔ)言體系也呈現(xiàn)出雜糅拼貼的特征。
如馮玉雷運(yùn)用了跨媒介敘事手法,對(duì)神話傳說原型進(jìn)行了跨語(yǔ)境移植與現(xiàn)代演繹。小說中,傳統(tǒng)的部落會(huì)盟儀式在現(xiàn)代語(yǔ)境下被微信交流平臺(tái)所取代,朋友圈、公告成為各部落間信息互通、商業(yè)貿(mào)易的新途徑。這種現(xiàn)代與傳統(tǒng)的融合,不僅為故事增添了荒誕主義的色彩,也反映了馮玉雷在全球化背景下對(duì)人類文明交流方式的深刻預(yù)見與反思。此外,馮玉雷還根據(jù)人物形象特征選擇不同的語(yǔ)言風(fēng)格。如時(shí)尚達(dá)人鯀常使用新潮詞匯,展現(xiàn)出其前衛(wèi)與潮流的一面;而恪守法制的獄官之長(zhǎng)皋陶則常用“敬諾”“圣上”等詞匯,凸顯其嚴(yán)謹(jǐn)與威嚴(yán)的一面。
值得注意的是,歌謠、文學(xué)片段、考古史料等多元文化要素的交融出現(xiàn),增加文本陌生化效果的同時(shí),對(duì)讀者的文化積淀也提出了重大挑戰(zhàn)。讀者在閱讀的過程中需查閱相關(guān)文獻(xiàn),才能將附著在文本表面的意義釋放出來。這種創(chuàng)作傾向,實(shí)際上是馮玉雷試圖打破現(xiàn)代快餐式閱讀模式,賦予讀者更多闡釋與注解文本的空間,進(jìn)而實(shí)現(xiàn)文化科普與文明溯源的目的。

注:本文原標(biāo)題《“重述神話”中探尋文化敘事路徑——論馮玉雷的<禹王書>》,首發(fā)于《西部文藝研究》2024年第三期。轉(zhuǎn)發(fā)時(shí)略有修改。
鄭瑩,蘭州大學(xué)文學(xué)院碩士研究生。研究方向中國(guó)現(xiàn)當(dāng)代文學(xué),海外華文文學(xué)。
- 2024-05-07【巡禮馬銜山】金聲玉振,玉說《禹王書》(三)
- 2024-05-09【巡禮馬銜山】馮玉雷:戈壁灘上的一片森林
- 2024-05-11【巡禮馬銜山】《禹王書》:文化英雄、民族精神與時(shí)代精神的多元呈現(xiàn)
- 2024-05-11【巡禮馬銜山】《禹王書》:文明溯源、詩(shī)性智慧和詩(shī)性真實(shí)的有機(jī)統(tǒng)一

 西北角
西北角 中國(guó)甘肅網(wǎng)微信
中國(guó)甘肅網(wǎng)微信 微博甘肅
微博甘肅 學(xué)習(xí)強(qiáng)國(guó)
學(xué)習(xí)強(qiáng)國(guó) 今日頭條號(hào)
今日頭條號(hào)











